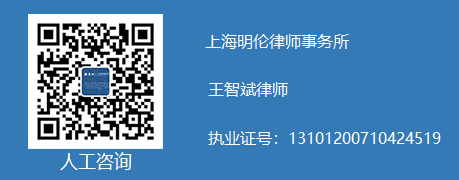贵州百灵预亏公告“迟到”遭股民索赔:未提前预告、年报突爆雷,信披漏洞何解?
近日,我们代理的投资者诉贵州百灵案已多批次提交法院立案,公开信息显示,此前贵阳中院已对部分投资者索赔案作出一审判决,贵州百灵因其未及时披露业绩预亏公告而被判承担赔偿责任,该案例对于证券市场有其警示意义。
“迟到” 的预告已构成虚假陈述
贵州百灵的违规行为,本质是触碰了业绩预告披露的强制性监管红线。作为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其 2023 年净利润由 2022 年的正数转为 - 4.15 亿元,完全符合沪深交易所关于 “净利润为负需强制披露业绩预告” 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公司出现此类财务指标重大变化时,需在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即次年 1 月 31 日前)披露业绩预告,该期限为法定强制要求,不存在任何例外豁免情形。
从法律定性来看,法院已明确将贵州百灵 “未及时披露业绩预告” 的行为认定为 “重大遗漏型虚假陈述”。《证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而公司净利润从盈利转为亏损,直接关系到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状况及股票价值的判断,属于典型的 “重大信息”。
更关键的是,法院在本案中确立了清晰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只要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2024 年 2 月 1 日,即法定披露期限届满次日)至更正日(2024 年 4 月 30 日,公司披露年报及亏损信息当日)期间买入并持有股票,即可推定交易因果关系成立。这一判决充分呼应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对中小投资者的倾斜保护原则。
被隐瞒的 “亏损炸弹”
对普通股民而言,贵州百灵的 “沉默” 绝非单纯的程序瑕疵,而是直接制造了投资决策的信息盲区,导致投资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额外风险。某投资者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基于公司此前连续十年盈利的历史表现买入股票,却未察觉公司已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巨亏,4 月 30 日年报披露当日股价大幅下跌,直接导致其本金亏损。
这种误导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打破盈利预期惯性。连续盈利记录易让股民形成 “公司经营稳定” 的认知,降低风险警惕性,而未披露的亏损信息恰恰是打破这一 “安全幻觉” 的关键变量;其二,剥夺风险规避机会。若公司在 1 月 31 日前按规定披露亏损预告,投资者可及时卖出股票止损或者暂缓买入,但贵州百灵的延迟披露将股民 “锁定” 在风险中长达三个月;其三,放大损失幅度。4 月 30 日集中披露的亏损信息引发市场恐慌性抛售,股价单日跌幅远大于风险逐步释放的情形,进一步扩大了投资者的损失规模。
法院最终支持的赔偿金额,已充分考量这种误导的实质影响。法院扣除部分仅为市场系统风险导致的损失,其余均由公司违规行为承担。这意味着,只要投资者能证明买入时间与违规周期重合,且损失与违规行为存在关联,其合理损失就能获得法律支持。
市场同类违规:三大乱象亟待整治
贵州百灵案并非个例,业绩预告违规已成为 A 股市场的高频乱象。据沪深北交所 2024 年 7 月发布的《2024 年上半年上市公司监管报告》统计,2024 年上半年全市场共 48 家上市公司修正业绩预告,其中 8 家出现‘由盈转亏’的业绩性质转变,2 家因更正后触及退市指标被实施风险警示。2025 年以来,业绩预告类违规仍呈高发趋势,主要呈现三种典型形态,且均对投资者权益造成损害:
第一种是延迟披露,如贵州百灵般 “硬扛到年报日” 的情况占比约 30%。典型案例包括百甲科技:该公司 2025 年 1 月披露 2024 年度业绩预告,称预计归母净利润 180 万至 260 万元;两个月后却修正为亏损 439.49 万元,不仅差异幅度超 300%,更涉及 “由盈转亏” 的性质转变,且未及时向市场解释差异原因,最终被北交所通报批评(据北交所 2025 年 4 月纪律处分公告)。这类行为往往伴随财务处理瑕疵,例如贵州百灵就被监管查出存在销售费用跨期结转、坏账计提不准确等问题,本质是通过拖延披露掩盖公司财务缺陷。
第二种是预告失实,这类违规更为隐蔽,易导致投资者误判。*ST 富润便是典型:公司 2025 年 1 月首次预告 2024 年度扣除后营业收入 3.06 亿元(高于 “营收低于 3 亿元” 的退市临界点),3 月 18 日却更正为 2.87 亿元,直接触及 “净利润为负且营收低于 3 亿元” 的退市指标,核心问题是未将 1904.14 万元与主业无关收入从营收中扣除(根据上交所 2025 年 3 月监管文件)。另一家公司 ST 墨龙则因财务核算错误导致预告失实:2025 年 1 月预告 2024 年净利润 4700 万至 6000 万元(拟将子公司股权转让收益 3.4 亿元计入当期损益),3 月 24 日却修正为亏损 3500 万至 4500 万元,差异额超 8000 万元,更正原因是年审会计师认定该股权转让为权益性交易,应计入资本公积而非损益(据深交所 2025 年 4 月问询函回复),暴露出公司财务核算的专业性缺陷。
第三种是随意修正,近年来逐渐成为新趋势。阳光股份的案例较为典型:公司因水电费等代收代付收入会计处理不当,将 2021 年至 2024 年三季度的收入确认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净额法,导致累计营收追溯调减,最终 2024 年扣除后营收仅 2.78 亿元,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根据公司 2025 年 4 月会计差错更正公告)。ST观典则存在多次收入调整问题:2025 年 1 月预告 2024 年营收 1.12 亿至 1.28 亿元,后续修正时调减近 2900 万元,虽披露原因是 “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未达确认条件的收入不予确认”,但公司此前已因 “未按验收单确认收入” 导致 2023 年多期营收调减超 4000 万元,反映出收入核算的系统性缺陷,最终被上交所公开谴责(据上交所 2025 年 5 月纪律处分公告)。
从监管层面来看,当前对这类违规的处罚仍以通报批评、出具警示函等行政监管措施为主,民事赔偿往往成为约束上市公司行为的最后防线。贵州百灵案的胜诉判决,不仅为股民维权提供了明确指引,更向市场释放出强烈信号:业绩预告的 “一字之差、一日之迟”,都可能触发沉重的法律代价。对上市公司而言,唯有严守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底线,才能真正维护市场公平秩序与投资者信心;对投资者而言,需警惕业绩预告 “变脸” 风险,一旦遭遇违规行为,应及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股民索赔条件:2024 年 2 月 1 日之后有买入且 2024 年 4 月 29 日有持股
律师观点: 业绩预告制度,旨在提前提醒投资者避雷,然而,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完全可以在季报、半年报中逐步体现,内容详实且信息正确的季报、半年报,完全可以让市场分阶段了解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成熟的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仔细阅读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提前避雷。会计年度结束之后发布业绩预告的必要性存疑。 更关键的是,实践中经常出现迟发、不发业绩预告或者临近年报披露期才修正的情况。如果上市公司存心误导投资者,股民们该踩的雷一个都不会少。 如果让我说,在加强对季报、半年报监管的基础上,取消业绩预告制度,对市场是更友善的,对股民也是更友好的。